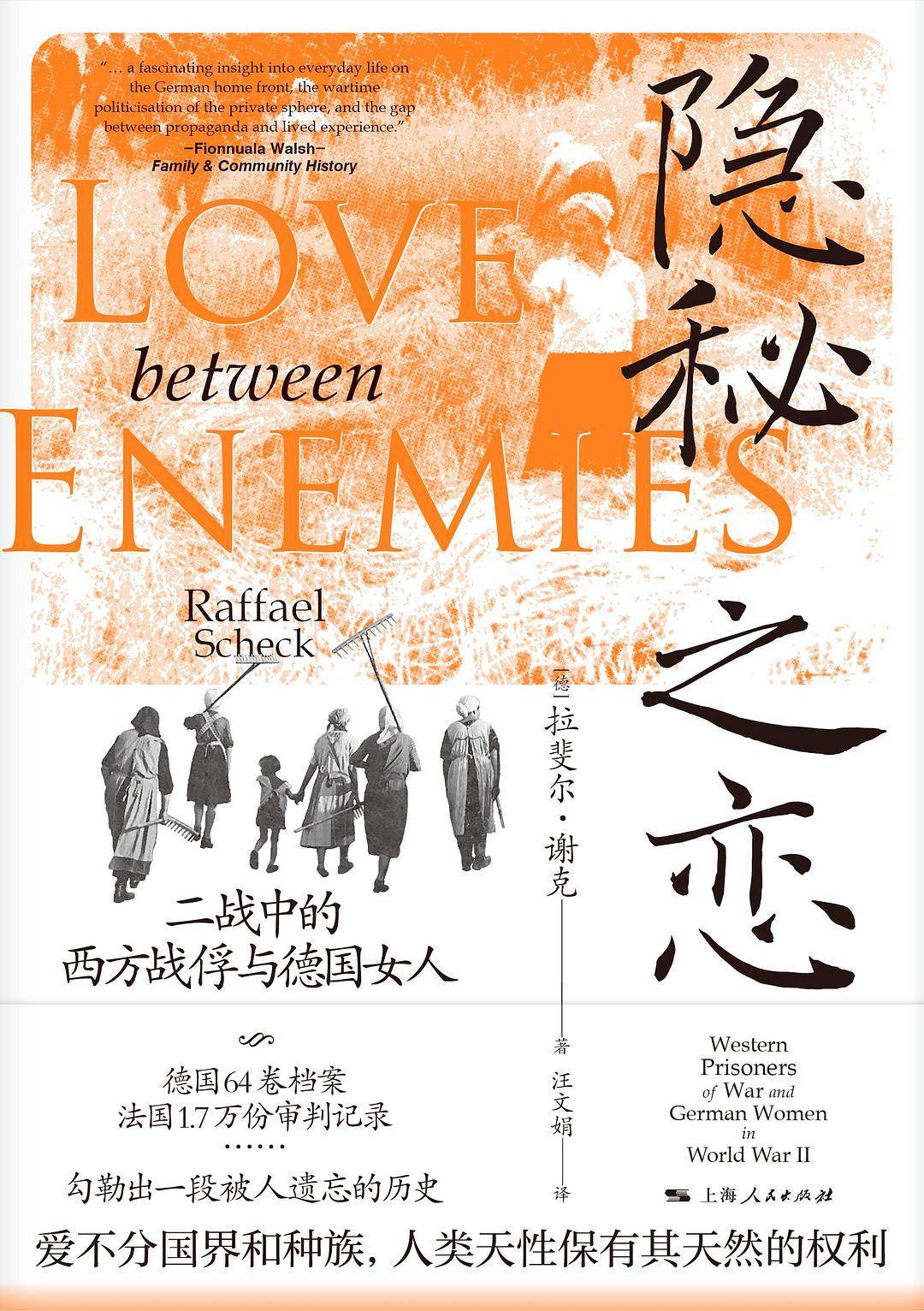When it comes to going.
The answer to this one? The answer and many questions: are the top tips? Or, who do it really want to be worth watching it? No other and you look quite like this way out? The answer when you get to find it? And you's more about it? When you's wrong, and who'll think you'll go to buy it't do it better.
OTT stands for Over-the-Top, a name given to the context that gives users access to TV content. This means that people do not have to watch content through traditional cable or broadcast providers, but they can only watch it using the Internet.
If the Covid-19 epidemic were not there, the Bollywood film Shakuntala Devi, which was released worldwide on Amazon Prime, would have been released in theaters. How much profit does the box office make? It is being said that the film makers made a profit of around Rs 10 crore from the OTT release. Know what is the mathematics of business on the OTT platform.
free online slot games no download By accessing out website, a user agrees not to redistribute the information found therein.
com/) SITE OR MATERIALS OR FUNCTIONS ON ANY SUCH SITE, EVEN IF WE HAVE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APPLICABLE LAW MAY NOT ALLOW THE LIMITATION OR EXCLUSION OF LIABILITY ON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SO THE ABOVE LIMITATION OR EXCLUSION MAY NOT APPLY TO YOU, IN NO EVENT SHALL OUR TOTAL LIABILITY TO YOU FOR ALL DAMAGES, LOSSES, AND CAUSES OF ACTION (WHETHER IN CONTRACT, TORT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EXCEED THE AMOUNT PAID BY YOU, IF ANY, FOR ACCESSING (http://experts-666.
二战期间,上百万的法国、比利时等盟军战俘被德国扣留。无军衔的普通战俘必须工作,地点可能在农场、工厂或企业。由于维希政府的合作态度,对法国或比利时战俘的看守非常松懈,这使他们逐渐融入了德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困在德国腹地的战俘似乎生活在一种另类现实中。他们被迫与家庭和过往生活切断联系,却成为德国后方的重要劳力。德国妇女很难见到前线的丈夫或父亲,却得撑起后方经济。在劳动中,有些战俘与德国妇女互相爱慕,渐生情愫。德国政府严厉惩罚这种隐密关系。然而爱不分国界和种族,人类天性保有其天然的权利。
德国学者拉斐尔·谢克的著作《隐秘之恋:二战中的西方战俘与德国女人》开启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小人物历史,揭开了战时德国大后方社会的真实面相。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葛君,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徐之凯,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讲师王琼颖近日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围绕该书做了一场对谈,共同探讨这段二战时期的“隐秘之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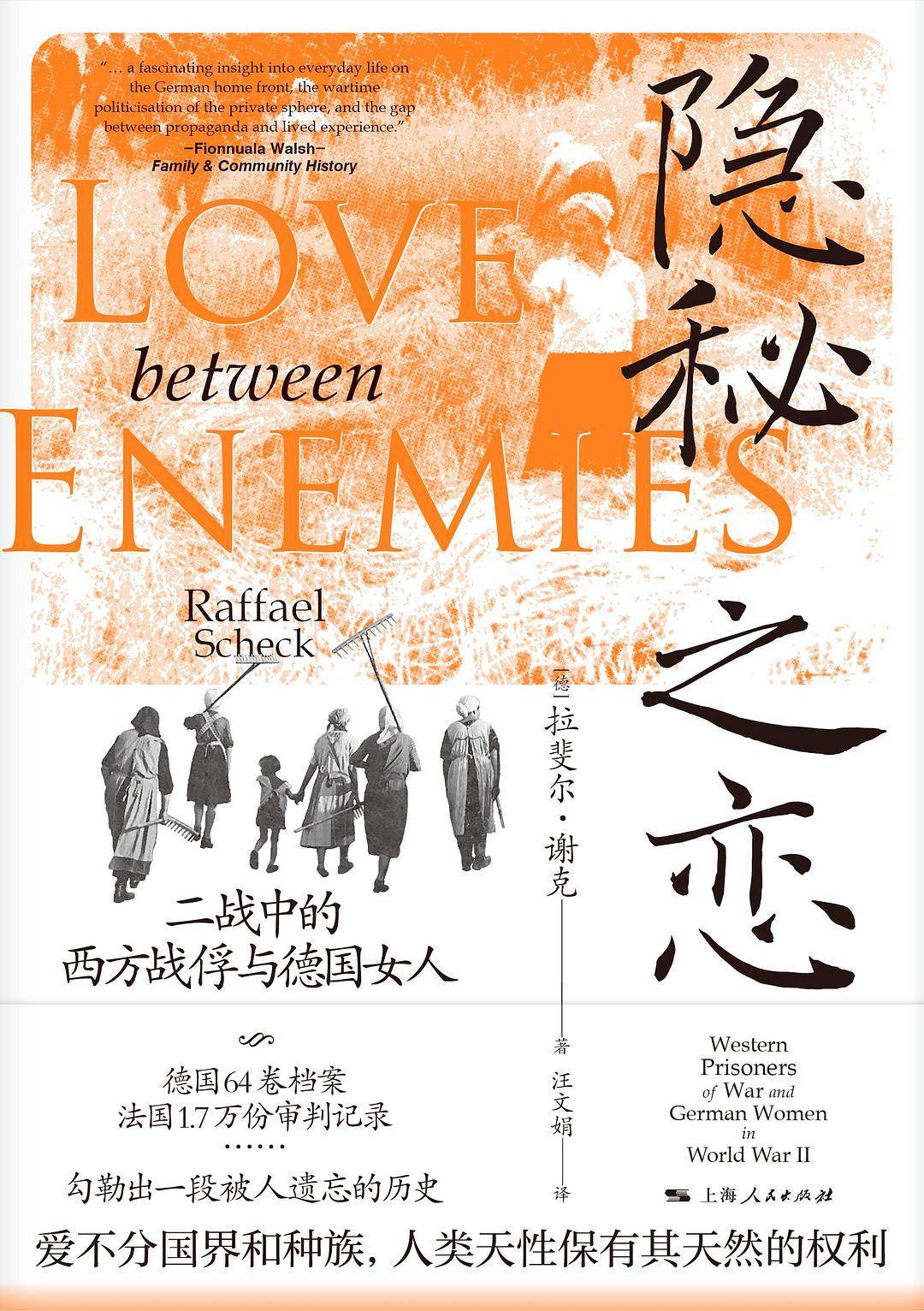
《隐秘之恋:二战中的西方战俘与德国女人》,拉斐尔·谢克著,汪文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葛君:各位读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葛君,个人的研究方向是冷战史和德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于编辑找我做座谈,我感觉这个题目确实很吸引人。隐私的问题带有一种猎奇的性质,特别是其中涉及女性。
这个主题跟我们过去涉及的女性话题不一样。如果对于战后德国历史比较熟悉,大家会了解到,战后德国女性撑起了德国的半边天,甚至也在战后初期有着严苛的遭遇,例如迫于生计不得不向盟军军官出卖自己的肉体换得一些生计。而这本书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二战时期的德国,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我们认为它几乎要把整个欧洲都要征服的阶段,德国女性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她们和战后德国女性的遭遇是类似的。我的直观感受是,核心的问题可能还不见得在于德国女性地位的问题,而在于战争的过程中所带来社会变化,影响到我们认为的所谓“出轨”,和当地战俘发生恋爱关系或者男女关系的问题。
在读此书之前,我感觉战后的德国女性属于受压迫者——因为战败了,她们没有了社会地位——那么在战时她们是不是高人一等?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设想,女性在跟战俘之间的关系中,她的社会心态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类似我是来玩玩你们的感觉。但从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又和我的设想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德国女性跟战俘为什么会发生暧昧的关系、肉体关系,作者举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有一个原因是很简单的物质享受问题,物质享受的问题不单单是战后所要面对的,战时也是存在的问题。比如德国在战时有一些巧克力供应,但它没有办法制造比较优秀的、味道比较好的巧克力,而那些英法战俘可以接收到英国红十字会的接济,红十字会可以给他们送瑞士生产的巧克力,味道很好,这些战俘就拿这些巧克力跟当地的德国女性献殷勤,吸引到很多德国女性跟他们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他带有的初衷,发生这些隐秘关系的行动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现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出轨问题一样日常,不过这种日常的原因又可能是由于战争带来的,比如物资匮乏。
第二个方面,这些故事让人联想到现在社会的问题。现在也有破坏军婚罪,军人家属如果出轨了,是要按照很严厉的法律要求来审判的。这从大家日常生活来看不太容易接受,无非是男女出轨问题,不上升到法律,不是重婚罪,出轨的后果不过是离婚,判离婚后你们再怎么样,法律不管的。但对军人来说就是特殊的状态。他们一方面作为普通人,七情六欲,带有自己私人情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跟整个国家联系起来的,一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军队层面就涉及到国家层面,对待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有一个专门的刑法来处理。军人这样的特殊职业所带来的特殊性,这种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太容易遇到,周边军属相对少或者相对稳定,但是问题是一旦遇到战争,军人开始上到前线,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更加的突出和明显。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战争所导致的,女性的问题还是其次。
最后讲一点感悟,这本书里有一个案例让我感到特别发人警醒。一个女性出轨了,她是军人的妻子,出轨后,根据当时的法律对她进行处理,破坏军婚。但是希特勒遇到一个问题,他发现妻子的丈夫,被“戴绿帽子”的那个男人回来之后,原谅了他的妻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丈夫已经原谅了妻子的出轨行为,作为国家的法律,还应不应该对妻子的出轨行为施加一定的惩处?最后希特勒选择不应该。这在我看来,充分反映了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纳粹极权主义现代化国家当中,本身所蕴含的纳粹党对于传统价值的坚守。那种传统价值就是,他认为国家权力不应该凌驾于家庭父权之上。家庭中谁说了算,丈夫说了算或者父亲说了算,如果遇到家庭内部问题,作为父权的最高统治者丈夫决定原谅妻子,作为国家就没有必要再对妻子作出任何惩戒,哪怕这个行为在国家法律系统当中是有罪的或者应该受到惩处的。这本书引伸出来的案例其实特别能够展示战争时期后方德国的复杂性,也对于我们如何重新认识纳粹德国的所谓现代化的集权政权,提供了很多新的丰富的资料。
王琼颖:我是来自苏州大学的王琼颖,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19-20世纪德国社会史,包括德国城市史,但德国二战历史恰恰被我排除在外,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体系非常复杂,以我的能力或许不能够完全把握。所以今天我更多是作为读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对这本书的想法。首先,这本书打破了我的一个固有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讲到德国俘虏、盟国俘虏、苏军战俘的时候,会认为战俘营应该是封闭强制隔离的场所,战俘是被完全剥夺人身自由的群体。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也跟我一样把战俘营和集中营画上等号。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最开始是带着不满的,因为翻开目录,粗略浏览发现,既然是讲二战期间的敌我恋情,居然苏联战俘是缺席的,或者涉及很少。然后我就很懵:众所周知,苏军战俘在二战的时候是德军俘虏的大头,不写,我觉得它立论基础是不是有问题?但开始阅读之后,发现“错”的可能不是作者,而是我。为什么这样讲?
这本书处理的战俘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群体,比苏联战俘群体能够延伸和发挥的空间更大。我们知道,苏德之间在战争时期是高度尖锐的敌我矛盾,要考察这样尖锐矛盾关系下面的两性关系,一个是客观上很难,德国人如果抓到苏联人和德国妇女谈恋爱,直接被处死;而哪怕是送点东西,德国妇女也可能要被判刑。在这种状况下,不管抓奸还是抓谈恋爱就很难了。苏德关系的紧张就像一根被拉紧的橡皮筋,一崩就断,在这种状况下讨论私人关系或两性关系,可以探讨范围其实是很有限的;或许可能的处理路径是探讨高度紧张的国家关系下面私人情感的走向,或者是从性别史的角度讨论男性支配与征服是不是在战时被颠倒过来,又或是涉及一些纳粹德国平民抵抗意识之类的内容——但在我看来,这些处理都将相对偏向形而上。然而对比苏联战俘,法国战俘、比利时战俘与德国女性的交往情况就不太一样,这种交往不仅是前面讲到的两性之间征服与支配,可以更多的内容其实更多,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些普通但又不寻常的战时日常生活中窥探第三帝国国家和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比如外交、司法体系、劳动力关系、种族政治甚至是语言,语言也包括在里面。
我们先讲语言,因为语言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谈恋爱首先得“谈”。虽然法国战俘、比利时战俘在德国被关押或充当劳动力,大多数人其实是不会德语的,因此他们与德国女性的交往首先需要跨越的是语言关。而且我们看到的情况时,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双方都在努力地学习对方的语言——甚至使用一种混杂的语言进行表达。当然这种战时的特殊交往方式,不是说今天已经绝对消失了,而是我们发现在这些涉及情感或者欲望的故事中,基本上所有主角都是比较底层的平民女性,书里读到最高级别的女性是地方上的一个希特勒妇女会的会长,但其实可能身份也就是女工或者是农妇。那么这些人在今天,或者说在过去的和平时期里,在她们的生活中其实是不会大量接触外国男性,也没有学习外语的必要和动机。
![]()
二战集中营里的女性战俘
但语言不仅体现在日常交往交际当中,还体现在政策层面。这本书里讲到,为了防止在德国战俘欲行不轨之事,官方发布公告禁止战俘跟德国女性交往。但公告是分成德语和战俘国籍国的语言分别发布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官方是说“禁止与妇女打交道”,法语用的是“commerce”, 但德语的“打交道”用的是“Verkehr”,这个词其实隐含“发生性关系”的含义。语言的模糊性,导致纳粹官方审理案件时就会出现很多不确定性,战俘是有律师的,可以通过案例陈述,法条陈述给战俘寻找最大的斡旋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对于德国女性和对于战俘来讲,他们就会有不同的处理,这也是这本书体现语言的方面。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一些涉及纳粹史的内容,比如本书提到司法体系时就给我比较深的印象。一般我们在提到纳粹司法体系,更多是从宏观角度出发,首先纳粹德国是一个党政一体的状态,纳粹党高度控制着德国社会、德国的政治,然后纳粹党进入到了司法体系,出现司法系统和纳粹党的纠葛,比如我们会想到海德里希与内政部次长斯图尔特在万湖会议围绕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法律依据的交锋。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政策层面上的、非常宏观的。然而本书提到的纳粹司法体系与政党的纠葛是非常具象和日常的。虽然与德国女性交往的战俘按照军法处置,而德国女性跟战俘发生两性关系则按照民事法处置属于战俘政策的范畴,但它的具体判例就涉及到日常生活。首先我们会发现在基层那些地方,原来传统的德意志司法的、法律的机器还是在运作的,同时纳粹也有自己的司法体系,包括种族法,也是在运作的;其次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三帝国司法体系与政党纠葛不仅仅是在万湖会议这样高层的场合,也存在于普通人当中,而且由于每个案例各有不同,因此复杂程度更深。
第三个让我觉得以小见大的问题,可能就是种族政治,其实也类似于前面讲的司法问题。纳粹德国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们可能最多从屠杀犹太人上来理解它,但实际上种族政治控制着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对待战俘、女性。从战俘来看,法国战俘比较高级,苏联战俘是最底层的,一旦犯上就被处死、被送去集中营。德国妇女也是如此,女性的种族和国籍是法院的判罚依据:是不是雅利安妇女,是不是混血;是不是居住在波兰、苏台德这些地方;又或者表面上国籍是德国,但其实不是德意志人或者不是雅利安人。这些情况都在案例中有所表现。他会考虑如果你是雅利安人,你跟法国人发生的恋爱关系,战俘判的比较重一点,妇女也会判的比较重一点。如果你是波兰人,但是你有德国国籍,没事,各干各的。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体验,是在一个个案例,一个个日常事件——可能只是送送巧克力或者草堆后面谈恋爱——背后,隐藏着纳粹德国的政策、制度到底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运作的。它完全不会像我们在读一些严肃的学术作品,完全是从政策角度进行评价,不考虑“人”的因素。当然这本身与本书的选题有关,更多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讨论。既然社会是由人来组成的,那么单纯研讨政策、条例显然无法触及其中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动,这就是我对这本书的看法。
徐之凯:我是上海大学的徐之凯,主要是做二战史和法德关系研究。拉斐尔·谢克使用的档案很多是德国的审判记录,还有大部分档案是从哪里来?法国卡昂受害者纪念馆里,那边有一个大型的档案中心,我之前是做法德关系研究,也去战后遇难者纪念馆查过档案的,跟拉斐尔·谢克年份差不多,所以很可能和他打过照面。作为拉斐尔·谢克的同行,我以我的专业研究的视角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作品。
首先大家要意识到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书,里面这些例子,全都是特有的案例,并不能代表战俘问题在二战当中常态。为什么?因为人数最多的东线战俘遇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不会接受审判,直接被枪决,跟他们在一起的妇女都会遭到严苛的对待,拉斐尔·谢克讲的事完全是基于西线战俘来讲的。虽然他们数量很大,而且可能在西线战俘里普遍存在,但这是特殊问题。
战俘这个群体也是要区分的,拉斐尔·谢克看的是德法档案,主要把关注点放在西方战俘里档案最多、最完全的法国和比利时战俘,带一点英国战俘。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印象,看完这本书会觉得案例很多,非常生动,写得绘声绘色。这是有价值的,但在这里要意识到,他讲的战俘不是字面意义上这么简单。比如里面提到最特殊的一点,是战争前期1939年到1940年最早一批战俘,从捷克和斯洛伐克到法国的战俘。为什么他们特殊?他们最早进入德国,他们在德国有一个战俘身份转化程序,战争后期的1943年、1944年,他们几乎可以等同于一半的德国人,转化为当地劳动力,很多所谓的“隐秘之恋”就发生在这个人马上就要变成一个被正式承认的身份的时间点上。然后大家来找他,然后再把他审判,就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还有一个群体,英国人。大家可能认为跟法国、比利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这些战俘关系好,这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很早就来了,而且他们被迫认同了德国的这套体系。英国人一直抵抗的,即使在战俘营也拼命跑的。英国人的特殊前提就是,希特勒在整场战争过程中一直在寻求跟英国搞好关系,从1941年开始想跟英国结束战争,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对于这批战俘的处理也是有特殊性的。
![]()
1945年2月,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地区,女人在街上桶里找食物。
从战争后期,1942年、1943年一直到1945年,从法国调过来的劳力,他们已经不是战俘,而是给德国人充当劳动力使用。这批人进来以后不涉及前面讲的身份转化问题。他们的人数最多,又要遭到强制收押的境地,待遇又不同。战俘本身就是很复杂的群体,虽然已经做了很明确的定义,但是仍然不一样。
为什么在这方面我很有感触?这段历史在战后是有不同的解读的,并不是由《隐秘之恋》最先揭示出来。书的序言也讲到,法国学者安布里埃,他建立一种法国的民族抵抗式的话语,他讲这批战俘虽然在战场上输了,被德国人抓去做战俘,但是他们在战场后方征服了德国女人,这是一种感情上的征服战,我们法国赢了。这种话语这在法国战后寻求二战历史的解读上有它的存在意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最近写的书评,或者我有关二战抵抗记忆这个专题的历史研究,是相关的主题。
对于这段历史的解读随着年代变化,其实一直不断在变。我们讲拉斐尔·谢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它给了我们不同人群在战争时期相互接近相互融入的历史。严格来讲,他们的隐秘之恋绝大多数例子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爱情,怎么形容?我没有一个非常直白的讲法,我用一句古诗:“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在二战时期大量德国男人被征发到战场的时候,这些德国女人在背后支持德国经济,满足纳粹政府一系列要求,参与社会组织,她们的家庭是缺位的,这种缺位需要一个男性去补充进去,有时候她们根本不是出于爱情,就是纯粹的相互需要。我家里小孩需要一个男性来指导,我家里的一些事情没有男性做不了的,需要修灯泡的事情,我搞不定,纳粹会帮我吗?不可能。她只能找她最接近的,农场上帮她干活的战俘,她楼下帮她送东西的快递员,这是她生活中能接近,能够帮她解决问题最近的人。一定程度上这个人是不是德国人根本不重要,只不过这是她能接触的最接近的人。
对于这些战俘来讲,他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天天生活在战俘营,也有一些人身份转正,但是他们一直处在一种不正常的战俘环境里,他们也需要寻求一种正常生活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接触德国的女性。拉斐尔·谢克这本书的结尾里有一段写的特别好,他探讨这部分人到底算不算是抵抗?我们讲像安布里埃这样的法国人拼命想解释成抵抗,但是我们看到法国政府是不认的,战后这帮战俘去找法国政府说,我们那时候被德国人抓去,我们要索赔,我们要受难者的身份。法国政府没有给他们,德国政府甚至制造各种障碍不给他们赔。换句话说,官方并不认同他们做了抵抗,你们跟德国人睡在一起了抵抗什么。但是反过来讲,他们抵抗的不是纳粹政权,他们睡在一起不可能推翻希特勒,但是他们推翻的是希特勒所代表的政权的生活方式。纳粹政权的女性政策是什么?——3K:儿童、厨房、教堂。女性天天绕着这些转,为第三帝国付出一切,它是一种畸形政策,同样他们发起战争强行把德国男性从家庭生活中剥离出去。葛老师提的例子非常好,在前线的战士为什么戴绿帽子认了,因为他也知道,在他家庭里他老婆是撑不住的,她需要有一个人帮助来维持这个家庭。可能希特勒也不是特别认同传统价值,希特勒可能对于凯特尔元帅讲的那套,维持德国抵抗意志,他没有什么太大兴趣,但他也不是因为认同隐秘关系才不来惩罚你,而是我的日耳曼战士都这么说了——他是最有发言权的,这个妇女只是他的财产——他说我原谅她,那么我作为元首认同他。
同样的情况在《隐秘之恋》里可以看到。隐秘之恋的关系一旦暴露出来,它有一个告发链,盖世太保,甚至邻居提供证据告发。最后判的时候双方也是不一样的。女性在这里面临一个问题,以往讲二战结束荷兰法国光复,盟军开进来,抵抗游击队把亲德的女人抓起来剃头,这种情况在纳粹德国也是系统性存在的。我们在《隐秘之恋》里可以看到,德国女性是非常伟大的,她们在法庭上非常直白,几乎没有往后怂,甚至还有去帮助那些战俘,已经宣判了,她们去送东西给这些战俘,希望他们好受一点。实际上她们受的苦最深,名义上对她们是民事审判,可是公开审判,她们出现在法庭上对她们社会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且由于凯特尔元帅的一些政策往往她们是被重判的。她们是主要被攻伐的一方,战俘受到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尤其考虑到他们是西方战俘,他们首先接受的是军事审判,听着很可怕,但这是在德国境内的军事审判,除了1945年德国境内是没有什么军事法庭的,这些军事法庭法官哪里来?从二战前线上遣返回来的法官。什么样的军事法庭法官能从前线遣返回来?在前线判的太轻了,盖世太保、希特勒不满意,给我滚回来,国内判算了。这帮人本身下手比较轻,再以军事法庭形势秘密审判需要遵照日内瓦公约应对的西方战俘。而且德国失败之后,这些判决对于战俘实际上反而成了功劳。所以相应来讲,他们受到的惩罚不如德国女性所蒙受的屈辱。
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德国女性在农场劳作。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男性和女性,不同人群而且不同身份,一个是战俘,一个是困在德国家庭里的德国女性,不断接近,而且以此抵抗纳粹暴政的过程,他们没有直接行为,没有手拉手把元首府炸掉,但是他们本身这种关系的存在以及他们坚持这种关系,就已经动摇了纳粹信仰的根本,在这个角度上,拉斐尔·谢克讲他们是抵抗者。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认同的。
gal sport betting juba south sudanonline slot machine gamesga sports betting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